常常与母亲共餐时,手握筷子夹书佐味。母亲每每看到我的痴样,总会将菜轻轻夹到我的碗里心疼道:娃,快吃饭吧,吃完再看不迟的。对于书的痴迷,于我的枕边餐案甚至卫生间的凌乱,总是母亲帮我无休止的收拾井然。我几近是个精神的饿殍者也是时间的吝啬者,常常心疼那些于眉间指缝无意滑落的零碎时光,于是我以书籍为钵,总能在有意无意间积攒到许多如细金碎银般点滴时间,这些珍贵的宁馨儿聚集着微笑着跳动在我的书本里幻化成行行蝇头,日渐丰腴了我的皮囊。
我是从“文化革命”走出的早产儿,一如我的名字也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迹。在那个狂热的红色年代,我却未能与“文化”牵手,疯狂革了文化的命。听着样板戏解渴,喊着破四旧充饥,物质的匮乏已然使我面黄肌瘦,知识的空白更让我成了行尸走肉。想要找到一些关于文学之类的书籍几乎无望。 初中时,常常为了买到一本诸如《故事会》之类的杂志,星期日步行几十里路踯躅往返于通往县城的铺满石子漫天尘灰的乡路上。那时候家贫,书资是平常捡废纸或橘子皮晒干卖给药房积攒下来的毛票,至于新华书店那些几块钱一本的名家诸作只能是望书兴叹了。
有一年暑假,去城里表姐家,表姐和我说:弟弟,你这么喜欢看书,可是家里真是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买书,姐带你去一个既不花钱又可以看到好多好多书的地方。就是那次,我知道了当时县城里唯一一个叫做“图书馆”的去处。整整五天,除了回到表姐家吃饭睡觉,我像一尾鱼游进了大海,这是我平生见到的最多书籍的宫殿。斑驳陈旧的书架上许多高尚的灵魂向我招手微笑,传递我生命的活力。我坐在海边等待高尔基放飞他的海燕;在月白风清的扁舟期盼与李白对饮踏歌;在风雪交加的除夕夜想为祥林嫂披上一件厚厚的棉衣。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从蛰眠的史韵中苏醒向我走来,为我展开精彩的画卷。
整整三十年了,每当想起那扇朱红的斑驳大门和门前那对怒目圆睁的石刻狮子,我的内心总会闪过一丝慌乱,仿佛那对石刻的狮子洞穿了我的内心。那一刻我仿佛是一个被脱光了伪装的外衣,赤裸站在精神法庭的被审判者。内心的虚伪、狂傲、名利、还有虚掷光阴的大度,在那一刻都惊慌得无所遁处。长期囚居于世俗惯于学会的掩藏和虚饰,伪装了内心的空虚和迷茫,使得自己很少直面自己的心灵。于是浮躁与狂傲替代了恬淡与虔诚。精神支柱的缺失,已将我和物质世界的迷恋画地为牢,一次次与信仰失之交臂。人可以不信神,但绝不可以缺少信仰。须知,在精神朝圣的路上,每个人只能是虔诚的匍匐者。很多时候,信仰的缺席往往是得到了时间和财富的默许。磨难是对人生、信仰的一种考验与抉择。
选择之于命运往往偶然,梦想之于少年定是天空。儿时的天总是那么蓝、那么朗,读了几本书就喜欢天马行空去梦游。少年的我最喜欢在那个纯净的天空下做着许多彩色的梦,梦想拥有一片自己的天空。很多次,我看见自己坐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宽敞书房里,面前是宽大的办公桌,背后是一排很大的书柜,两边也是书柜,柔和明亮的灯光照着我,温暖着书柜里摆放整齐的我的挚友和桌上我的文字以及被文字融化的心。我喜欢纸媒书籍捧在手里的那种踏实和真实感。走进那片天,尘世的纷扰已离我渐行渐远,灵魂走出了躯体。仿佛----我是一尾流浪的鱼,正穿过诗经的河流游离在屈子的故乡寻找着诗人的脚印。大唐的诗宴已然开席,婉约的宋词正在唱和。我带着我的心赴约一场旷世的盛宴。徜徉在书海籍浪,我叩响一扇扇厚重的墨香之门,膜拜一个个高尚的灵魂,与他们作一次长久的心灵对话。或悲悯济世、忧国怀家,或豪放形骸、吟风歌月;或淡愁浅思、秋月春光。这些来自心灵深处最真实的声音感染着我,涤荡着我,陶醉着我。
偏居一隅,一方斗室,几排书柜,不必奢华,但真实且属于自己。每本书都是一位心仪已久的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清谈浅语中,采菊煮清茗,蜂蝶戏桃花。松下落棋子,溪上浮流觞。罅隙白驹过,怡然不知归。书外是流年的俗世,打开书,尘扰已恍然隔世。拥有这片天,寄存流浪的心,放飞今生的梦,复夫何求?
人生是一本书,有厚也有薄。生命串起了线装的书脊,岁月将文字点缀成章装订着精彩的每一页。思想赋予文字灵魂在生活的浪花中淬炼文字的韧性,用时间作墨抒写成章。每一页只是岁月长河中的断章。在如水的日子里,我们艰难跋涉,每一步都踩出一个声响。或欢歌或悲叹、或离愁或泯笑。生命的响动飞溅激荡,落地成行。于是人生的书本变得充实丰盈起来。
每个人就是自己的作者,每本书都有着各自的精彩与经典,社会就是陈列收藏的图书馆。一本书、一道风景;一行字,一串人生的足迹。我们陶醉在风景里,同时也陶醉了别人的眼眸。毕生我们都在这座浩瀚的书馆里汲取营养、修行自我,匍匐膜拜在朝圣的路上。在这里我们阅读着他人,书写着自己,努力让自己的人生不再潦草败笔。拥有这片天,用虔诚与感恩通过文字,在人生的彼岸开垦一片精神的净土,播种爱的种子,用善良浇灌出一片天然的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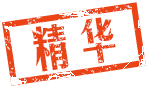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