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这几天偶有时间,翻到近百年前胡适之先生在《新青年》关于此的论述——《贞操问题》,其精彩与评述,让今人尚感振聋发聩;对男女平等与人格平等理念的解读与分析,就那些男权作宠的男人给予了理性的批判与规劝。
关于贞操方面的话题,可能是个永远的话题;老木在某个QQ见到一些网友也曾深深地讨论过,最主要的是几个没有进化到现代人的男人们的那种“处女情结”,他们可以与女子胡来,而他们则要求自己的对象必须是第一次与己相好;这种要求简直不可理喻,可是在他们看来,却是自然得天经地义。当时老木很想说几句,如果自己是,就有权利要求对方是,也可以不要求对方不是;如果自己不是,那就没有任何理由来要求女方是处女。
社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有这样的要求,体现了价值的多元化,应该是好事。在观念与言行上,我们的心胸是不是可以容忍异端,是不是可以与不同价值信仰的人和谐相处,这是关键所在。如果一个人的心胸狭隘到除了自己的是正确无误或近似真理之外,容不得别人或异议,那么这种心态与心胸是应该得到鄙弃的。所以,在今天,有人可以要求,有人可以不要求,但我们更多的提倡有序、有性道德、有人格的宽容,不予要求。
在胡先生的论述中,他着重叙述了几件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生死事小,失节是大”“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未谋面的未婚夫病死了,女子就要守寡终生或是殉夫”。而亲人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对抗,是守旧的表现,是应该抛弃的,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权。
程朱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当然也是后儒学时代的一个理念,“存天理,灭人欲”,看似有道理,但其实是违反了天理。人欲即天理,灭人欲就是灭天理,何存天理呢?在没有辩证地与正反的分析与看待的时候,这种风气竟然在中华土地上娼行了800年之久,幸亏来了一场史无前例且最重要的辛亥,通过这样的洗礼,让我们开始反思并逐渐融入现代文明社会。这样的表述,并不是提倡人欲张扬,更不是容忍无序的乱欲,而是我们要将这种不合天理的东西毫不留情地抛到历史中去。老木曾经的邻居,年老的寡妇就是这样的牺牲品。可见,我们还有多少的路要走。
胡先生对于贞操状况进行了不断的梳理与分析,而不是一棒子打死,特别是不断地细化。胡先生用“输入学理”之法,指出了问题所在,同时也指出了解决之道,这是老木特别尊崇的地方,他不仅在“贞操问题”方面,而是在太多的方面,如政治、社会、信仰、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胡先生对社会鼓励烈女的行为给予了抨击,给社会环境给予了指责,给政府提出了建议,给不当法律给予了建议与修正方法。这是胡先生高于他时代文化界、思想界所有人的高明与过识之处。
我不知道,为什么胡先生的著作并不为人所知?而我们习惯于随便接受观点的草民,别人说这个家伙不是好鸟,我们根本不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立即就觉得这个家伙不是好鸟。再多说几句,对鲁迅的尊敬是仰之弥高,可是过了青年时期,又看了胡的著作,两者比较来看,各有所长,但就促进社会进步而言,还是胡先生的实用主义更为的得力得法,就目前而言,胡远在周先生之上,鲁迅认识了问题的严重,也表达了,并没有指出解决之道;独秀认识到问题严重,可他也说了,不过他过激了点,如胡先生说《文学改良刍议》,陈先生说《文学革命》,陈四次入狱,胡先生四次尽力施以援手,当然不施援手,陈先生性命也无可忧……
就贞操问题,仅仅看胡先生的《贞操问题》而理解胡先生深邃思想也只能理解个皮毛,还要看他的《易卜生主义》《美国妇女》等许多文章。
附《贞操问题》
一
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人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受了几千年的无意识的迷信,到近几十年中,方才有些西洋学者正式讨论这问题的真意义。文学家如易卜生的《群鬼》和Thomas Hardy的《苔史》(Tess),都带着讨论这个问题。如今家庭专制最利害的日本居然也有这样大胆的议论!这是东方文明吏上一件极可贺的事。
当周先生翻译这篇文字的时候,北京一家很有价值的报纸登出一篇恰相反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海宁朱尔迈的《会葬唐烈妇记》。(七月二十三四北京《中华新报》。)上半篇写唐烈妇之死如下:
唐烈妇之死,所阅灰水,钱卤,投河,雉经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则其亲试于杀人之方者凡九。自除夕上溯其夫亡之夕,凡九十有八日。夫以九死之惨毒,又历九十八日之长,非所称百挫于折有进而无退者乎?……
下文又借出一件“俞氏女守节”的事来替唐烈妇作陪衬:
女年十九,受海盐张氏聘,未于归,夫夭,女即绝食七日;家人劝之力,始进糜曰,“吾即生,必至张氏,宁服丧三年,然后归报地下。”
最妙的是朱尔迈的论断:
嗟乎,俞氏女盖闻烈妇之风而兴起者平?……俞氏女果能死于绝食七日之内岂不甚幸?乃为家人阻之,俞氏女亦以三年为己任,余正恐三年之间,凡一千 八十日有奇,非如烈妇之九十八日也。且绝食之后,其家人防之者百端,……虽有死之志,而无死之间,可奈何?烈妇倘能阴相之以成其节,风化所关,猗欤甚矣!
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俞氏女还不曾出嫁,不过因为信了那种荒谬的贞操迷信,想做那“青史上留名的事”,所以绝食寻死,想做烈女。这位朱先生要维持风化,所以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烈妇的英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这种议论可算得贞操迷信的极端代表。《儒林外史》里面的王玉辉看他女儿殉夫死了,不但不哀痛,反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五十二回)王玉辉的女儿殉已嫁之夫,尚在情理之中。王玉辉自己“生这女儿为伦纪生色”,他看他女儿死了反觉高兴,已不在情理之中了。至于这位朱先生巴望别人家的女儿替他未婚夫做烈女,说出那种“猗欤盛哉”的全无心肝的话,可不是贞操迷信的极端代表吗?
贞操问题之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在文明国里,男女用自由意志,由高尚的恋爱,订了婚约,有时男的或女的不幸死了,剩下的那一个因为生时爱情太深,故情愿不再婚嫁。这是合情理的事。若在婚姻不自由之国,男女订婚以后,女的还不知男的面长面短,有何情爱可言?不料竟有一种陋儒,用“青史上留名的事”来鼓励无知女儿做烈女,“为伦纪生色”,“风化所关,猗欤盛矣!”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这不过是贞操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真相,已经与谢野晶子说得很明白了。她提出几个疑问,内中有一条是:“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这个疑问,在中国更为重要。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分。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怪不得古人要请“周婆制礼”来补救“周公制礼”的不平等了。
我不是说,因为男子嫖妓,女子便该偷汉;也不是说,因为老爷有姨太太,太太便该有姨老爷。我说的是,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
为什么呢?因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这并不是外国进口的妖言,这乃是孔丘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丘说: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孔丘五伦之中,只说了四伦,未免有点欠缺。他理该加上一句道:
所求乎吾妇,先施之,未能也。
这才是大公无私的圣人之道!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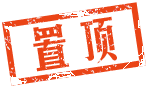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