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帖最后由 萧若秋 于 2011-5-22 14:33 编辑
盖房
1982年的秋天,二舅骑着他刚买不久的飞鸽牌自行车,从40里地外的李家庄一路飞奔到他姐姐家。当时我爹和娘正在昏黄的地里拔着一把把带着露水的黄豆秸子,纯净蔚蓝的天空里还微微透着些凉气。一脸汗水的二舅远远地朝着空旷的田野里的两个黑影喊:姐――姐!姐――夫!声音激越高亢,仿佛黄土高坡放羊娃唱得信天游。娘吓了一跳,本能地以为娘家出了什么事情,惶恐不安地立起了身子。爹刚好捆起了一扎豆秸,停下手里的活,从兜里掏出了包大前门,等二舅到了面前也顺势递了根烟给他。
二舅在田头支起那辆蹭光闪亮的自行车,等抽完了烟,檫完了汗,于是他说,他要盖房,需要借钱。
那年二舅32岁,刚刚娶了舅娘,两口子除了种地,家里最值钱的也就是屋里养的两头母猪。二舅的房在村的最西边,是一栋摇摇晃晃,土胚加青砖砌成的老屋。老屋是李家祖父手里的财产,历史久远,从旧社会到新中国,横跨了半个世纪。到了二舅手里,他就筑了道土墙把老屋隔成两个房间,前边是灶堂,八仙桌子,两张红木椅子。后边侧用石板,砖头垒成一个猪圈。猪圈右边搁着一张木梯,木梯是通向小阁楼的温馨的婚床。每当过年在二舅家吃值年饭,一桌的人一边喝着酒,夹着菜。一边听着里屋的猪仔谗得嗷嗷直叫,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很热闹,也很有趣。
二舅终于还是拿到了钱。娘是从衣柜里搬出一个梳妆盒,从里面拿出用牛皮筋扎得整整齐齐的五叠花绿的钞票。二舅把两扎十元的钞票放在里面的口袋,又把三扎五元的钱放在了另一个口袋。他说姐那我就走了,走时哼着曲儿,忘了和我爹打招呼。他一走,爹和娘就吵了起来。我爹是拍着桌子吼:日你娘娘的,你把钱都给了这个杂种,我们家还要不要过日子?再说这狗崽拿了钱何年马月还啊。娘只说,他会还的,接着就不作声,躲一边去,端着木盆,拿着棒槌,去后屋的水塘洗衣服,那青石码头上蹲着满满的大姑娘,小媳妇,洗衣的洗衣,淘米的淘米,还有嗓子美的小姑娘在唱歌。水面上荡漾着一池塘的欢声笑语。爹再窝着火,也不可以学蛮横的二流子,总不能按着自己老婆的头往水里摁,我爹就站在码头岸上,跺着脚,生着闷气。爹倔强的神态很滑稽,把那些池塘边的大姑娘小媳妇若得笑弯了腰。
自从挖地基开始,我们家就开始和二舅一家栓在一起了。娘提前两天就住进了舅舅家里,开始安顿工匠们的伙食。瓦匠是从孙家村来的,领头的叫大海,这名字听起来像电影里的英雄,大海老婆也跟着来,是干小工,我爹也是干小工,还有一些二舅的朋友以及舅娘都是干小工。四个瓦匠兼带着这么多小工,这简直与大日本皇军一样,一个鬼子带着三四个伪军。组织起来也象模象样的一支建筑施工队,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二舅的脑海里充满了,毛主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伟大思想。其实在现在的我看来不为别的,也就为省两钱。
毕竟舅娘小,当时只有20来岁,是个还在做梦的年龄。眼见门前堆放的乱七八糟的材料,心情也随之糟糕起来。当那些泥水瓦匠们带着各色家伙进驻二舅家,很快打破原来生活的宁静,并随之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要去找几根细钢丝,去竹匠那里买起脚手架的毛竹,去木匠那里削些木钉,等等琐碎的事情,不胜其烦。二舅见舅娘从原来的期待与兴奋中走入了烦恼的深渊。于是开导舅娘说:现在有瓦匠,还怕个啥?原始人类都是靠自己两只手盖得窝,不照样干得成,我们现在可是强多了。
动工那天,我爹和二舅拎着夯地基的铁疙瘩,死命地喊:嗨约,嗨约。那块桑树地很快变成了几条深深的交错的壕沟。石子,黄沙,水泥包,砖头,水泥预制板,东一堆,西一堆,像淮海战役里的战场。瓦匠师傅们伸着个瓦刀,把一块块砖头敲得叮当作响。大海老婆则在大师傅旁边递砖头,一块接着一块,远远看去好像一条自动运输带。我娘和舅娘,一个拿着锄头铲子绊水泥浆,一个提着铁皮桶给师傅们递着弹药,我也试着拎过一桶,铁皮桶看起来很小,可是装上一点泥浆,就变得很沉,很沉。
建房是快乐的,尽管有点苦,有点累,但大家都有说有笑。那时候还小,听不懂那些泥水瓦匠的黄色段子,只知道连我娘和舅娘听了也一起捂着嘴笑。可是这样的美好时光才过了一天,舅舅的梦想就被一个叫李锁根的同村人给搅得七零八落。
对于李锁根,是没有防备的,因为李锁根就在我二舅的西边,距离上算起来还是个邻居。第二天早上8点的样子,工地刚刚开始恢复了点忙碌。一个穿着蝙蝠衫,喇叭裤的胖女人站在水泥包上吹起了进攻的号角。起初干活的谁也不在意,直到有人去铲水泥,那女人还和菩萨一样纹丝不动,才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劲。女人张口骂的就是:李法坤啊,你这个婊子生的,你在挖你自个家的坟啊,这坟够大啊,够你一家三口都躺里面啊。。。。。。女人声音很大,八里地外的人都听见,于是村里的,路过的,上到80岁的老头老太,下到3岁娃娃,都像鸭子一样伸长了脖子过来看热闹。
二舅说,你再骂,再骂我就不客气了。
舅娘也站在黄沙堆上,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指着那女人,但她只会骂一句,你是个卖X的。你是个卖X的。
李锁根带着两个弟兄,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手里拿着铁铲,过来就摞倒了刚砌好的半米高的墙,二舅和我爹就过去夺家伙。锁根举着铁铲狂吼:你过来,过来,我就辟死你。
二舅捡了块砖头砸过去,砸了锁根的脸,锁根人哼了一下,就倒下去了。我爹和一平头男的也滚在了一起,二舅几个朋友很快加入了战斗。胖女人和舅娘互相抓了起来,一边抓,一边骂,一边哭,一边叫,两个女人的头发都变成鸡窝。我娘天性就胆子小,见了这场面,身子就一直不停地抖。直到舅娘好看的瓜子脸出现了一道道血痕,娘才去拉那女人的衣服,连骂带哭。旁观的有来劝架的,但不知道怎么是拉错了人,还是早有预谋,很快也加入混战,场面一度壮观失控。后来就没人敢来,都在看热闹了。每到惊险处,人群都还会发出一阵奇怪的叫声。82年还没有设110,就是喊警察,警察也只是骑个自行车来。效率肯定远不如现在的汽车。真正先来劝架的到是李家村的村长和大队书记。来解决问题的时,他们都是度着方步,不慌不忙地过来的。
李锁根被痛击后,成天躺在床上喊痛起不来了。二舅的房子也别想砌,锁根女人天天搬张小凳子,坐在高高的水泥板上,唱戏一样骂着山门。瓦匠们等了两天见没什么好办法只好鸟兽散去。天一天冷似一天,新房还是那半米不到的墙,看起来到有点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后留下的味道。那些和好的水泥浆,泡好的石灰,经凌厉的寒风一吹,都冻得比石头还硬一点。期间王书记来了两趟,带回了那家的意思:一,李锁根的伤得治,二,要砌房子西边墙必须缩回去三尺,要不会影响他家的日光。二舅的意思是:一,我法坤老婆的伤谁来治,那是毁容。二,只能缩回三公分,三公分就不影响日光,干吗要缩三尺。缩三尺连地基都要重新打。王书记是个和蔼的好人,听舅这么一说,一时也拿不下主意。只好又跑去锁根家,锁根打架吃了亏,现在恨不得马上地震把二舅家削平了,听了王书记一番阐述,所以坚决不答应。王书记就像猴子一样在两家窜来窜去,事情也没有个结果,不过好处到还是有。李锁根家给了他一条大前门,我二舅也给了他条大前门。这个算不上行贿,不为别的,就觉得理都在自己这边,要的是王书记能说句公道话。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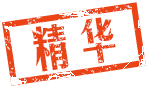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