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故乡,虽在江北,却有江南的特色,水多,稻香,米白,鱼鲜。在贫困年代,周遭村民连大米都见不到,我们却可以吃到浓香洁白,如珍珠般光滑的大米饭。这全得益于村南的一条河——大沂河。
大沂河很长,长得望不到尽头。在我们儿时的心里,她就是天上的银河,无边无际,神秘莫测。后听大人说,它的源头,远在山东沂蒙山,东到东海。具体有多长,我是没概念的。
河边设有渡口,那是去外村的通道。一老年艄公,每天早起晚归,忠于职守,风雨无阻摆渡。很像沈从文笔下翠翠的爷爷。而大沂河的景致,绝不逊于湘西的风景。过渡时,一群群人,扶老携幼,小心翼翼走上小木船,老艄公不停地叮嘱:小心点,别掉到河里了。船刚离岸,只听远处高喊“等一等”,船上人多时,老艄公就会扯着嗓子回答:“等下一船吧,人太多了。”喊叫声在水面上飘荡,惊飞了远处的野鸭。若船未满,老艄公就会把船划回岸边。每次坐在船上,身体随着小船在河面上荡荡悠悠,我都会惬意得如神似仙。抬头,成群洁白的鱼鹰,闪电般,在空中翱翔;平视,清清的河水随着艄公荡起的双桨,泛着涟漪;远眺,成片的芦苇,随风摇曳。近观,老艄公一前一后挥动的手臂,就像画家挥毫泼墨,随心所欲,那是多美的一幅山水画啊。而我,看到清清的河水,总是忍不住用手划动,常遭到老艄公善意的责怪。
大沂河,更是孩子们快乐的天堂。盛夏酷暑,男孩子们不胜炎热,呼朋唤友,三五成群结伴河边。三下两下除去身上的背心裤衩,光溜溜地跳进河里,扑通扑通,下锅的饺子般,水花四溅。兴致来了,还打起水仗,你泼我,我泼你,水声、笑声、喊叫声,溢满河道。女孩子比较腼腆,不能和男孩子一起疯,常臂挽竹篮,卷起裤腿,赤着双脚,在河岸边拣河蚌,时而弯腰,时而前行,时而停下,羡慕地欣赏着河中快乐的男孩们。河蚌拣回家,母亲们会煮出一锅锅乳汁般的汤,味浓鲜醇,喝在嘴里,齿颊余香,那是我们喝过最鲜最美的汤了。
儿时的冬天,极其寒冷,大沂河冰冻起来,真有毛泽东的“千里冰封”的气魄。整个河面,就像一块巨大的水晶石,河封,摆渡停止,村民就从冰上通行,骑车的、步行的,胜似闲庭信步。我们小孩子家是感受不到那种快乐的,大人怕有危险,是万万不许我们去的。
有水就有鱼。大沂河的鱼多,且鲜美。拿到集镇上去卖,周围村民会争先恐后购买,边买边说:“大沂河的鱼就是鲜。”我们村有很多捉鱼技术高明的人家。撑一叶小舟,漂行水上,一人摇橹,船声欸乃,一人下套(一种网状的捉鱼工具),套提起又放下。卡在套孔里的鱼,被取下,扔进船舱,活蹦乱跳。有时为了驱赶鱼儿,他们还会敲击船舷,梆——梆——梆的声音,在河面上一起一浮,碰上高兴,他们还会吼上几嗓子家乡的小曲。
秋天的傍晚,夕阳西下,我常常站在高高的河堤上,欣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景致,真是美不胜收。
离开家乡许多年,大沂河也渐行渐远,可它的美景无时无刻不在眼前浮现,大沂河的水,仍在心头淙淙流淌。我知道,故乡的河水已经融进我的血液里,不管我走多远,她一直陪伴着我,从春到夏,从秋到冬。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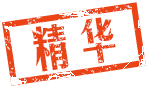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