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时光溢出自身的轨道,倒退着向我走来。一些尘封的日子逐渐开始清晰,不知不觉,我已经活在记忆里了。
那个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奏古琴曲《太古遗音》的古琴演奏家陈雷激先生,受作曲家刘湲邀请,曾于1990年的冬天,携法国夫人安娜与混血儿子陈养和来丹小住。
出于对文学艺术的崇尚与向往,陈雷激及其家眷的到来,给原本已经热情高涨的一帮朋友带来了新的欣喜。尤其是胜华兄长(道可道)倾其所有的真诚招待,在那个年代对于禳中羞涩的我们来说更是难能可贵。朱大可在〈古琴.被尘封的大音〉一文已略有记叙。现在想来仍然倍感珍惜。
许多美妙、欢喜的交谈、演奏,已随岁月淡淡模糊。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影响我以后人生态度甚至轨迹的,却是陈雷激先生法国夫人安娜的一句话。记得在谈到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这一类话题的时候,安娜用生硬却很深刻的中文说“我们、要、努力、摆脱、社会化、的、人”。
起初,我并不明了安娜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更不明白以后的岁月为理解这句话所付出的代价。当安娜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尽管有点如梦方醒,却依然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以我们那时开门办学所学习到的知识,要想完全领悟安娜这句话的道理,是困难的。但我至今仍然记得安娜那淡远的眼神与超然的口吻。
三十岁,是人生的上升期,精力饱满、精神旺盛。可以说正是入世拼搏、奋斗的时候,而我却过早地受到出世的影响。安娜的一句话似乎为自己的懒惰、消极找到了现存的理由。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我一直迷迷糊糊地在努力摆脱所谓的社会化,但什么是社会化到至今我却还是一直弄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我从来都没有从根本上进入过社会。如果说社会是一个圈,那么我就是一个一辈子都游离在这个圈子外面的橡皮人。一个生活在社会外面、完全与社会绝缘的人又从何谈起摆脱社会呢?
对于安娜那句话的理解,从那时到现在都是断章取义、莫名其妙的。乃至于有时把自己弄到啼笑皆非的境地。其实,摆脱社会化,并不是摆脱现实,对于社会,也并不是不参与。摆脱,不是人生的逃避,而是应当积极地去了解,知道其规律,然后努力使自己能很好地融入,找到自己的定位,去完成人生的轨迹。
多年来和老季兄茶余饭后的交谈,更多的是回顾与总结我们所走过的路。其实当我们把自己原本没有的身段再放低,把原本不是很高的道德门槛再提一提,心里应该还是豁然开朗的。虽然自己还没有到盖棺定论的年纪,但是人生的大半辈子已经过去,现在来谈出世入世这个话题,未免有些苦笑的成分。想当年,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啊。
有一点,多少可以慰藉自己的就是,在面对诸事诸物时,心态虽然不能完全清静下来,但努力“不动心”确是我这么多年来努力坚守的一个原则。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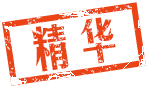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