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帖最后由 萧若秋 于 2011-8-15 16:32 编辑
许久没有失眠得如此歇斯底里。
凌晨4点,我倒汲着拖鞋站在天台楼梯口的大窗子下,巴望现时这细如娥眉的初月能渐渐填满,变成铜盘。占据大半窗子的梧桐树上,几条小细腿蹦来蹦去,活脱脱一皮影戏——麻雀们已经开始叽叽喳喳地讨论今日早餐的内容。在走廊尽头的水管以平均1滴每秒的速度漏完整一小时水后,我重投回温暖的床铺。
这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儿。上高中那会儿,我就经常把老牛(老班)的脸在视觉上与讲台凌空架开,模糊,锐化,然后放大,再放大,直至双重影像叠加到一起,再无限缩回原型。
可见,亲眼看到的瞬间未必就是真实,它是生活。
毕业两年了,朋友们求学的求学,成家的成家,工作的工作。我属于散漫自由的一类,上班,读书,旅行,一样都不能少。始终坚持,既然身体和灵魂不能常常同行,那么总要有一个路上。于是,当我在床上慵懒看片、超市悠闲购物的时候,惊觉这驻守在城市的同年人已经轮番烫起成熟的卷发,登上7厘米高的高跟鞋。和朋友喝茶的八卦话题开始改变,关心起彼此的实际未来,连在窗边瞥见一溜弯青葱的初高中生们,也会没来由地感叹风景不再。在我看来,相机日记能够记录的不叫风景,彼此铭记在心的才是。青春,只是逝去的先天风景;后天的纯真,在放弃与世界对抗后才能抵达。更多时候,我愿意化为一个玻璃瓶。装酒醇香装水清冽,空瓶的时候就是留白,透亮。
揭开记忆中的旅程,浮现在眼前的是当时的情境。同样的风景,不同的名字,异样的是情境——大哭、大笑,抑或是严重的沮丧。我承认自己不喜欢旅行套餐,拘泥于流程与格式,抹杀了人性中的单纯快乐,代之以疲乏,心的疲乏。若一个人感到乏困,所有的风景便在眼前上下浮浅,波纹回动,最后同化成远处的一道边境线,消逝在天际。当我还在咿呀学语的时候,我就学会伸出双手,试图抓住这若隐若现的情绪光圈,享受并回味。我贪恋这世界所赋予的泣鸣与欢快,乃至瞬间的温暖。
于是,在计划好行程后,我便携带这欲望上路,渴望着纯粹的感知。只有欲望简单了,才能减少对世界的索取,幸福也就在血脉里传承;对于日月的困苦,也认命地担当,视为一生的必然。周国平说,人生是一场无目的的旅行。无目的其实就是单行,可以转弯但不能调头,不必调头。那只是那段旅程所产生的情绪,故事是附属品脉络。就像喜剧电影《17 Again》中的设定一样,你还是会作出同样的抉择,演绎重复的情境。虚无之间的摇摆震荡,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旅行。
清朝有一种白玉腰牌,无字无图,纹叶清晰,温润透水头。
仿若蓝姆的文字,笔底温润,笔力十足。
我想,那才是我的追求与归宿。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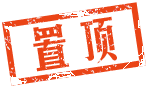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