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既亡 剑客拔剑的时候,春秋很乱。记得,许多故事都诞生于春秋。把时光的画面拉近一点,把旋轴打开来,春秋更像一种张牙舞爪的画面,弱女子往往献给昏君,忠臣良将公式化地颠沛流离,抹着血泪等待着下一次的崛起。唯有诗歌,从不慌张。偶尔冲动一点,也属于不朽的那一种。 第一次有诗歌冲动的时候,我不到十四岁。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风从对面的湖面上掠过,微微凉。那时,我躺在我兄弟家,一张有着数十年包浆的竹椅上,双脚朝着南方,翻看着一本叫《七种武器》的武侠书。心智很不成熟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了“别离钩”。 那一瞬间,很想写诗。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写诗可能来源自内心一股汹涌澎湃的冲动,始作俑者必定是南方年少无知的血。以至于后来,单位组织义务献血我总是第一个报名,可能也隐含了对诗歌的某种惩罚与回归。诗歌需要痛苦。可是那时的我没有。甚至我连泪水也已丢失了好多年。我当时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开始丧失流泪功能的。即使我最亲爱的外公,他去世的时候,我也掉不出一滴泪。最后在一片器乐哀鸣的抽泣里,我听见自己内心深处的责骂,责骂自己为什么只有楚囚的痛苦,为什么没有楚国痛苦的眼泪。其实,我很痛苦。真的。然而,痛苦并不代表当时我能流泪,能写诗。即使摆到现在,摆到明天,流泪写诗绝对是一种境界。我当时真的不会写。写不出。连背都背不出几首。 “别离钩”是一件厉害的武器。别离竟然可以作为武器。当时敲破脑袋都想不通的事,如今一一在过去找到了答案。有时,我也想,忘记了过去,是不是意味着过去也忘记了我。这句话,算不算一句诗。如果算,我还想说,青春为什么总是在疼痛的别离中逐渐长大,发芽?家乡的桑田为什么每年都要到冬天进行疼痛的修剪?那每年的春蚕秋蚕,它们在白色的丝里,累吗哭吗痛吗?为什么母亲总要在冬天,搜集着丝瓜南瓜冬瓜的种子,沾上南方的雨露,细心地洒在燕子别离的路上?为什么父亲总要在夏天,撑起竹篙驾起木船拍打着南方染在水波里的晚霞,年复一年照料着稻子麦子韭菜青菜疼痛的别离? 那时的南方没有烟尘,天空很蓝,语言的污染远没有现在严重。别离对于青春来说,是宿命,更是另外一种海誓山盟地相逢。村前的柳树下,青石板前,诗歌以另外一种青春的形式,诱惑着我。青春的结局没有卡夫卡的悬念,我在别离的一本书中,爱上了诗歌。 十四岁。平生第一次学会别离父亲母亲。第一次学习写诗歌。虽然离家只有十几里,但寄宿在烟雨迷蒙的南方学校,和门口野草、野河相伴,青春的热血常常会肆无忌惮地横空出世,借以装扮比热情更热情比冷漠更冷漠的青春痘。 青春的梧桐树长在岭上多白云的深山,想它的时候,树下自然就会听见紫色的诵经声。其实,在纯粹的梧桐树下,而不是呆头呆脑的法国梧桐树下,我甚至听到过白色的叹息,黄色的忧郁,黑色的微笑,蓝色的从容。多年以后,一位80后美女作家花容失色道:诵经声竟然也有颜色?其实,道理很简单,就像现在的我,行色匆匆地陪着妻子逛在帝国的某个商厦,根据心情搭配着自己喜欢的服饰颜色,红的绿的,very much。揭开谜底的答案和白开水一样乏味。所以,在梧桐树下,听到声音和读懂声音绝对是两个概念。成长的诗歌拒绝一切似是而非中庸式的读懂。 超喜欢那时的诗歌精神。 超喜欢。 每一种指点的手势,每一处南方遗忘的江山,和宿舍里台湾灰姑娘方季惟挂在墙上冷若冰霜的脸,都是诗。都是诗啊。 父亲发现我诗歌的时候,没有丝毫表演性质的犹豫,而是直接气吞山河地撕成碎片。从物质的表象看,父亲的世界从来就不相信诗歌。父亲义愤填膺地用右手第三个手指头的中关节,狠命地敲打着桌子。他相信勾股定理,笛卡尔定理,悬浮漂浮对流,比现实更现实的分数。还有,比分数更波澜壮阔的命运。 我把写诗改成了晚上,通宵,不敢达旦地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江桥腐朽已动摇,挥一挥手,带走所有的云彩。终于,又被父亲发现。垃圾!两个耳光,用的是右手,重重地打在我左边的脸颊上。五道血痕。可是没有泪水,我。父亲。 我一再强调左边的脸颊上,其实也没有更深刻的含义。是到后来,深谙力学的我,无师自通地测算出了父亲左手和右手发力点的功率不同。我后来反复用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分析,正因为父亲的发力点有着梅花三弄的有情有义,才使我没有像我的偶像张曼玉,像她《新龙门客栈》里那样斩钉截铁地“离开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 父亲连夜用行草写了一幅古诗贴在我左面书桌的墙上: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又连夜在右面的墙上,用行草写了一幅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末了,还用红色的圆珠笔,描绘了一颗语焉不详的篆书名字。也许是父亲隐藏多年的笔名。或者是更具境界感的法号、道号。 字贴在墙上以后。父亲双手背在身后,远看像宋江,近看像陆游,都有些像。明显属于宋江路线的父亲站在那幅字前很久,口里反复喃喃念叨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那一刻,我甚至怀疑正在学习《毛选》第五卷的父亲,对诗歌一定怀着革命般的痛苦。既然是革命,总要有人牺牲。在父亲精心布置的庙堂、江湖、革命错综复杂的青春舞台情境里,我内心顿时莫名地升起史诗般的悲壮.。在南方诗歌的枪炮中,我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一将功成万骨枯。直到很久以后,即使我坐在循规蹈矩的办公室,忙碌一些道貌岸然的公务,只要回忆起父亲对我十四岁的诗歌革命,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撅起灵魂深处的屁股,向着北方,三叩九拜下去。 因为我知道,君是君,臣是臣,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我是千百年来那些南方小吏被折磨的重复。 没有诗歌的青春开始在预先设置的发条里,做着F=ma的加速运动。牛顿在书本里秀完三次运动定律般的波浪式头发以后,青春的热血已经如今年的天气一样,开始急剧降温。但蚊子不会跟着诗歌的季节走,总有些时刻会伴着英文单词来恰到好处地问候一下how much。 真实的南方,夜晚和青春一样焦躁。只有那盏悬挂在头顶的白炽灯,明亮地,不动声色地等待着宿舍窗外蛙鸣、蛐声茉莉花革命式的复辟。复辟声还真有。一声,两声,吱吱地。不像个人,更不像南方的雨声,甚至更遥远的诗歌呻吟。打开门,是一只本地的毛脚蟹,有些害羞,有些不知所措。我把它放在脚盆上,给它明亮,自由,一米不到的自由,然后怀揣理想,和它一起复辟了一个诗意的夜晚。那个夜晚,我开怀大笑。并且,第一次深刻无情地掌握了“狞笑”这个词的深邃含义。 门再一次关上以后。被毛脚蟹复辟过的物理化学开始如嵇康一样慷慨赴死,而一贯故作城府的立体几何线性代数则更像司马昭。对,像司马昭一样痛哭,哭声传遍了洛阳城。我在古文中拼命检索着有关洛阳的词语描写,与诗歌无关。我看见了洛阳在一片冰心的北方。 耀眼的北方。 万丈光芒。 深夜。字典里的洛阳告诉我,对于不穿诗歌外衣的我,打开一扇门,迎接一只迷路或者梦想复辟诗歌的毛脚蟹,和迎接一个明眸皓齿千娇百媚脉脉含情的绝色女子,已经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区别。不是想与不想的问题,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形式主义害死人。真理只有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形成普遍经验,才能放之四海。灯光下,政治考卷最后一道论述题(40分),题目赫然为:论北方为何有倾城。 南方不产诗歌,是母亲告诉我的。 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南方正下着雨。母亲便学着村前菩萨庙面前许愿的语言叹气,说我来到人世的时候南方也在下着雨。然而,沉陷于力学结构分析的我已经学会了故作成熟地忘记诗歌。我会用材料力学弯矩试验帮不上忙的禁指,微笑地指着南方,看,妈妈,南方四百八十寺的钟声,全部在x轴y轴z轴三维空间里,敲打着南朝并不结实的大厦呢。母亲于是会表情惊讶地凝望南方。之后,我听见南方诗歌里的雨,滴答滴答地落在母亲柔弱的肩膀上。 多少个夜里,母亲总是独自坐在那张紫红色的官帽椅上,手捧着那盏刻着苏麻离青的高仕杯,静静地望着窗外的月光。我曾经端着一杯水走过面前,听到了母亲天籁般的低吟。我大惊失色。母亲一定是懂诗歌的。比父亲懂!她把诗歌一生的语言,用粗糙的双手丢在了窗外,埋进了土地,还给了月光,只留下,比沉默更沉默的沉默。 丢失了诗歌的我,正如丢失掉泪水的我,已经不记得多少次连南方的雨也想丢失掉。直到一个同样的深夜,同样的月光,同样的窗外,我坐在同样的官帽椅子上,捧着同样的高仕杯,才惊异地发现,母亲的诗歌里竟然满是苍白的雨水,哗哗地下着。下了整整十年。我十四岁就冰冻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原来我也是盛产泪水的。那一刻,我终于才知道。 南方竟是如此苦命。 南方,十年了,请原谅我轻狂的十年。南方,请原谅我埋在土里一直不敢吟唱不敢思念的诗歌,原谅我渺小的激昂,坚硬的踌躇。请原谅我,苦命的母亲,不要让十年的光线拽得越来越远。请原谅我,父亲,不要沉默地像母亲。不要。真的,都不要。 南方,原谅我失去诗歌的十年,原谅我沉醉不知归路,情绪低落纸醉金迷,喝酒唱歌通宵达旦打牌。原谅我,这一次用的真是通宵达旦这个词。父亲打在我左脸颊上的耳光,功率开始发酵。我知道那五道血痕越来越长得像一行诗歌了。一行白鹭上青天。那是唐诗。 今夜很冷。这里不是荒城,没有侠客,也没有别离钩。深夜喝酒的人很多,但我确信,喝酒寻找诗歌的,只有我一个。我仍在城北的那个大排档喝酒。喝了白酒以后,只能喝啤酒。丰姿绰约的老板娘比谁都懂我的眼神。其实,她从另外一种高度更懂得诗歌。结账以后,门外北风呼啸。北风里飘着雪花。啊,那一定是北方唐朝的诗,一定是诗歌化成了北方的雪。雪冷冷地打在脸上。好冷。冷又怎么样。 现在时刻,凌晨1:00。大排档门前的十字路口,南方的黄灯依然在闪烁。出门左拐,直行,就是洛阳的北方。我仰起脖子,喝完了拎在手里的最后一口酒,然后砸碎了瓶子,“砰”地一声挺胸,迎着寒风,迎着北方,向前。 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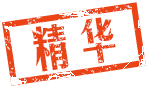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