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丹阳刀客 于 2011-6-17 12:39 编辑
2、徐东文
早晨,徐东文透过办公室窗户,一眼便看到少年细蟊坐在村口碌碡上,好久都没动弹。徐东文走近窗户,把脸紧贴玻璃看。为了看清楚些,徐东文对窗玻璃哈口气,抬手用衣袖擦拭一番后,又细细看了一阵。那显然是一个陌生少年。他好奇,这个少年是如何出现在坝下村的。这让他暗自兴奋,决定要与这个少年聊聊。
坝下村被四周的高山围着,生活寂静得像处在水底一般。每天哐当哐当响着从村边驶过的火车,更加衬托了坝下村的静。除了静,还少有外人出现。在徐东文十年坝下生活中,也只有五个人外人而已。这五个人,还是县里派来慰问的文工队。也只仅仅演出了一次,便不再前来。坝下在丛山峻岭之中。西边,距邻省小城榆树萍有两百多公里路。东边,距县城也有一百五十公里。人们进山、出山,要沿着坎坷曲折的羊肠小道行走,花费一周时间,绕着山转、沿着山爬,进出一次都要剥层皮。修铁路,是村庄形成几年后的事。那时,人们都说铁路修好后,坝下交通会便利。呼地一下就到了县城。等铁路修完,人们发现那根本是白扯。因为坝下没车站。哐当哐当驶过的火车,是坝下村人眼里的一道风景。可以看,但没法上。
坝下村在地图上出现,带着偶然性和特殊性。很少有一座村庄,因某个人的某一句话形成的。但坝下村就在随意性的一句话里诞生。十年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县革委会领导为打造知青模范点,把县城青年引进深山老林去修筑水坝。嗯……就在这里吧。县领导在决策时,把指点在全县地图的某一个地方说。这句话,决定世界上将增加一个叫坝下的大村落。那时,没坝下村这种叫法,只有山脚四个知青点,近千号知识青年。那些知识青年,初进深山时热血沸腾,扛着机械设备、生活用品、口粮以及玉米种子,一路高歌往深山里挺进:革命的口号溅满了泪花,迈开阔步!立即出发!不许回头更不许说话,广阔天地把根扎……但时间不到两年,便被单调繁重、艰苦危险的生活击败。在设计中,水坝长五百米,几乎要靠知青徒手修筑起来。知青们很快认清一个事实,没有机械设备、专业技术做保障,仅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建起水坝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消极的看法很快在知青中蔓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们热爱革命,但必须活着革命。修建水坝需炸山取石。知青开石组第一次采石,因宕口一哑炮忽然爆炸,当场炸死五人,乱石滚下砸死一人。炸碎的身躯与石头一起从天空落下,血肉模糊瞬间就让知青们本能地忘记了革命。他们如同后来的徐东文一样,原想将革命紧紧贴在生活上,但死亡将革命与生活硬生生地拉扯开来。在别的知青点为珍宝岛战役写血书时,坝下村的知青已热情大减,一边开展革命需要活着的私下讨论,一面梦想回到原来生活的县城。到了这时,他们才发觉进山容易出山难。出山,不是说背着行李、带上干粮就行。必须向县知青办公室打报告,回城后才能成为革命体制里的人。邮递员每月进山一次,带来、捎走知青书信。邮递员带回的回城申请结果不乐观。县领导惦记着水坝修筑进展,放下狠话,作为全省知青模范点,不把大坝修好,没人可回城。一句话就把坝下知青搁在山里。知青剩下的事,便是在山里混着日子等待。知青点便多了乱七八糟的事。打架时常发生。还发生过数次山火,都被扑灭,没把知青点烧毁。后来随着一些年纪大的知青开始谈起恋爱,知青点刮起男女恋爱之风,刹不住。很快第一批孩子出现。知青点慢慢变成了村庄。还好,县里虽痛心疾首,但没坐视不管,在坝下村建了一所小学。这反而让知情寒心。有了孩子还是不能回城。 如同细蟊,徐东文也是主动把自己扔进坝下村的。
徐东文是坝下村学校的老师。当初主动要求到坝下村小学教书时,徐东文没想到人生会滞留在这里,同那些知青一道被大山困住。两年多时间,再没人肯到坝下村小学来。县教育局不是不管。每年老师分配时,总会让一个年轻教室到坝下村学校报到。可没人愿意带着行李、食物,沿着铁轨走上一个星期,跑到深山里来。他们更愿意在城市里革命。那时,坝下村已在全县声名远播。人们都知道那里是一个模范知青点,同时也知那是可怕之地。这种认知,也是革命与生活的一种脱离。徐东文两年前凭一腔热血,写下血书光荣地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但作为前车之鉴,成了最后一个吃螃蟹的。为此,徐东文既是坝下村学校校长,也是学校唯一的老师。坝下村孩子多。知青们被困在山里,没事可做,脾气越来越燥,便一股脑生孩子。孩子越来越多。坝下村学校是一所小学,有八十多个学生。还有许多没到入学年龄的孩子在村里跑着。徐东文看着那些孩子,便会憎恨,暗骂这些知青无布尔什维克思想,只爱操女人不爱革命。那水坝修了十年,还没个屌形,革命在这里成甚样了。 徐东文想到坝下革命。但坝下村在山里风吹日晒十年后,革命色彩已相当淡了。 徐东文虽是校长,但在坝下村没一点地位。似乎哪一个村民都比他厉害。这一点,徐东文第一年到坝下时就有了见识。那时他在革命上热心,对调皮的学生,经常上门家访。其实他在夜晚也闲得很,无事可做,借机与知青们谈谈消磨闲时。但那些家长不把徐东文放在眼里。徐东文谈革命时,有些村人拿出纸笔,随便写一道微积分题、力学题递给徐东文说,这题解法我忘了,你解给我看看。徐东文这个中专生哪里会做。徐东文觉得受了侮辱。这种侮辱不是针对他徐东文个人,而是针对整个革命。这些坝下知青,得好好地评判教育。为此,徐东文暗中给县革委会写了许多信。但在这种大肆侮辱中,徐东文慢慢看清,在这些村人中,潜伏着各种各样的高才生。有学土木工程的,这些村民的住房才有棱有角、冬暖夏凉。有学医的,这个村庄的人才能不被知青医疗组所误诊,健康活着。有懂植物学的,人们才会把山涧湿地变成一块稻田。每年秋天,山里的水稻黄橙橙的,风吹稻浪起伏,发出沙沙声响。这缓解了坝下人口越来越多的吃饭难题。靠山里几十亩玉米地,坝下村是活不下去的。搞艺术的人也不少。知青点画主席像,徐东文看着一个村人在石头墙上搭张梯子,不消一个小时便成了。甚至在一个夜晚,徐东文听到山谷里传来天籁般的歌声。女人用俄语唱罢,又用汉语唱。徐东文听懂了,那个女人在深山里用美声唱《喀秋莎》。这是禁歌。徐东文初听时有种巨大恐惧,就像躲在被窝里收听敌台一样。继而为自己找到了理由,宽慰自己,听是为了揭露和评判。再说,这人胆子太大,革命思想到哪里去了,这行为就该批判。但恐惧感始终存在,因为他发现自己被这歌声吸引住了,甚至最后承认这歌声美妙,希望那女人能再唱一遍。
徐东文终于认清两点:一是他在革命不彻底的坝下村没甚可骄傲。二是村人对他带着恨。恨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不是知青,有一份工作和收入。
徐东文也甚是恨这些知青。你们这些狗日的,哪里想到别人痛楚。背着人,徐东文会斯文不顾地骂。因为等徐东文到了谈婚论嫁时,发现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女人可谈。山里的女知青,全让男知青捷足先登。而山外女人,又惊恐于坝下村的名声,不敢跟教师徐东文恋爱。徐东文没法,每年给教育局写信,要一名年轻女革命同志来坝下。未果,还落下笑柄。每到教师分配时,县教育局里就有人说,徐东文又要写信讨交配权了。这话很恶毒,哪里像革命同志所说。徐东文甚至想写一张大字报。 知青们恨徐东文,徐东文恨知青,但他们愿望又无限一致。盼着县里把知青点撤了。徐东文的布尔什维克思想,也像件外衣从身上剥落。革命归革命,生活归生活。坝下村恶劣的自然环境,给了这位热衷“砸烂旧世界”红卫兵一次认知馈赠。虽然革命与生活剥离,但徐东文仍旧维持着很好的革命形象。穿着整齐的中山装,头发用发油抹得很服帖,胸口像章擦得一尘不染。徐东文把自己与那些不修边幅的知情区分开来。 放下革命思想后,徐东文感到了无聊痛苦。徐东文喜欢站在窗前看火车。不像那些村人,就坐在铁轨便看。那是给革命抹黑啊。坝下村学校就建在铁路边。从学校后窗,可看到火车飞奔的身影。是客车还是货车,何时到来,这些悬念成了看火车的一种乐趣。客车时速有一百公里。只是数秒钟的时间就消失在视线里。火车上的人影看起来很虚。徐东文没有坐过火车。每当客车经过,他便想,是什么样的人坐在上面呢。这种想法牵出了许多痛楚。只是实在无聊时,徐东文才会玩这种痛苦的猜测。
当他看到细蟊坐在村口碌碡上时,心里是兴奋的。很好,终于有了一样新鲜东西来到坝下村。(待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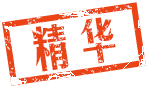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丹阳新闻网(https://www.dy001.cn)
( 苏ICP备05003163号 )